1943年夏,我在蓝田(今涟源)考入国立师范学院英语系,距今年正好一个甲子,昔日十六岁的少年今已近耄耋之年。蓝田光明山是国师及一脉相承的湖南师范大学的发祥之地。回忆蓝田旧事,心潮澎湃,思绪万千。
在江山半壁沉沦的苦难岁月里,教育家廖世承先生呕心沥血、披荆斩棘,在僻处湘中山区的蓝田创办了国师,并在那里艰难地坚持了六年之久(1938—1944)。后因敌骑逼近、炮声可闻,始被迫播迁湘西溆浦,抗战胜利后再迁南岳。解放后经过一些波折,师院发展壮大成今日的湖南师范大学。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下,国师在蓝田惨淡经营的六年却显示了辉煌,与随后略走下坡路的溆浦、南岳阶段比较,可说是黄金时期。在“宏施教泽”精神的熏陶下,蓝田小镇一时也成为抗战后方一颗灿烂的文化明珠。
光明山是蓝田镇旁边的一片青翠的山丘,清澈的涟溪潺潺地从山侧穿过。在经费拮据、物资匮乏的条件下,这片山林竟在短短时间内被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化气息的美丽高等学府,这真是湖南教育史上的奇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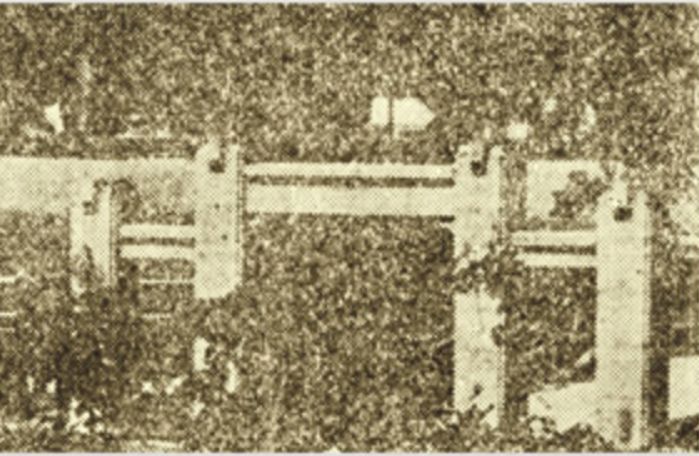
国立师范学院蓝田前门
美丽的光明山
我还记得,走出蓝田小街的石板路不远,国师宽敞的体育场就首先呈现在眼前,这是当时湖南省最标准的足球场和跑道。然后一条平整的林荫道把我们引向绿树丛中的校园。人们评说,国师的校舍在风格上是儒雅大方、朴实无华、不落俗套,呈现现代色彩。在布局上是依山坡傍松林修筑,高下得宜,错落有致,花木掩映,组成和谐的图画。在效果上,高等学府的文化气氛融入了美丽的大自然中,浑然一体。光明山最令我难忘的是:学殿巍峨,松涛入梦,幽谷听琴,涟水戏波……
“学殿巍峨”是指耸立在教学区山坡上的图书馆。说“巍峨”当然有些夸大,但是它是当时光明山以及蓝田最高大的建筑,中有拱门、拱道,很有庄严肃穆的气派。初次看到它时,我年轻的心真的被震撼了,因为我1938年在长沙时看到过被敌军野蛮炸毁的湖大图书馆,也经历过“长沙大火”。我仿佛看到,被我视为神圣殿堂的地方在后方又重建了。尽管大小规模无法与湖大图书馆相比,但这具有独特现代风格的崭新建筑使我看到了民族的新生和希望。在大楼内常常座无虚席的阅览室里以及两侧一排排宽敞明亮的教室里,我们曾经贪婪地啜饮着知识的圣泉。

国立师范学院图书馆阅览室
“松涛入梦”是指光明山有名的松涛声。宿舍区靠近后山的大片松林,风起时激起的涛声很有韵味,若天籁之音。猛烈时则若惊涛骇浪,使我们猛省,在神州破碎的日子里,要立志救国、发愤读书,不可稍懈。
“幽谷听琴”中的幽谷是指联谊社(包括联谊厅和音乐专修科的钢琴教室)所在的小山坳。联谊社后倚幽林,前临陡坡,可以在走廊和旁边草地上放眼穿过两旁的青山眺望远处的田畴、溪流、群山……风景如画,使人流连忘返,音专姑娘们悠扬的琴声更使人迷醉。清晨和黄昏时分,我常在这里读书或与学友们聊天。“论诗幽谷里,朦胧若有悟”,我这两句诗说的也就是当时的情景。

国立师范学院联谊社
“涟水戏波”也常常使我魂牵梦萦。我后来曾经濯足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和许多江河,但总忘不了国师那清澈明亮有如水晶的天然游泳池,那就是光明山下涟溪较宽较深的一段水流,但更衣、救生设施却很齐备。搏水涟溪是学子们最快乐的时刻。
高质量的教学
其所以说蓝田时期辉煌,最主要的还是指高质量的教学和良好的学风。学院在此时期名师荟萃、盛极一时。抗日战争期间大批知名学者教授迁往后方避难,经廖世承先生竭力罗致、恳切延聘,来院者甚多。各系都有名噪海内的学界泰斗,人才济济。教授阵容最强的属国文、教育系。国文系可称为汉语、经学界“宗师”的就有钱基博、马宗霍、骆鸿凯、宗子威、钟泰等教授。教育系的教授如孟宪承(“部聘教授”)、黄子通、郭一岑、高觉敷、储安平等都是社会科学界的名流。我没有机会也没有资格去亲听国文系诸大师的教诲,但有幸部分旁听过孟宪承教授讲授的教育哲学。他以流利的英语对杜威等人的教育哲学、思想源流作了详尽的分析,并且条理异常清晰地介绍了西方哲学概况。这不仅丰富了我的知识,对我在高年级时直接阅读外文原著亦有很大帮助。学院其他系也敦聘了一些名教授,如史地系讲授中国现代史的李剑农先生,讲述西洋史的皮名举教授等。我偶尔也抽时间旁听他们的课,感到他们学识渊博,论点精辟,很令人钦敬。国师在建校初期就集中了那么多学界精英,教学质量自然就有了高水平的起点,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众多良师的诱导和熏陶下,发愤图强、勤勉苦学的学风同时逐渐树立起来。

廖世承院长与部分名师合影
我们英语系的师资力量比不上国文、教育系,但同学们引以为荣的是钱基博教授的公子、学贯中西的钱钟书先生,在蓝田时期曾任英语系主任。遗憾的是我没有在钟书先生离校前听过他的课。好在先后继任系主任的沈同洽、汪梧封教授早年分别留学英、法,都有真才实学,也都是循循善诱的好老师,对我帮助很大。还记得,讲一口地道英国口音英语的沈教授富有风趣和幽默感,讲课时绘声绘色,把课文中的人物都讲活了。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他讲英国小品文“Seeing People Off”(《送别》)时的情景。汪梧封教授后来教我们英国戏剧、诗歌,他讲英语带浓厚法国口音,但对英国文学的了解很深。到我四年级时,他是我写毕业论文的导师。那时英语系学生一般都是翻译一本书作为毕业论文。我想试着用英文撰写,题目是《论华兹华斯与大自然》,汪先生给予了我热情支持和具体帮助。结果,这篇英语系可能还未有人尝试过用英文写的论文居然完成了。现在回忆起来,在内容和文字上都未免有些幼稚,但我在写作过程中得到很大锻炼。

钱钟书 英语系教授 英语系主任
在蓝田时期,国师的学术空气比较浓厚。各系都组织有学会,经常举行精彩的学术报告,并发动同学们为琳琅满目、各有千秋的壁报投稿。学校主办和同学们集资自办的学术性或其他期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有季刊、月刊、半月刊甚至旬刊。据我们年级毕业纪念册记载,蓝田时期学院拥有一千订户以上的杂志达七八种,有两种半月销售量曾突破三千份纪录。这在当时来说是了不起的成绩。有人说,国师学生喜欢“读死书”。此话不正确。虽然勤勉好学蔚然成风,而且战时蓝田比较闭塞,但师生们并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抗日战局和时局的任何变动都是大家息息相关的事,对天下事、国家大事的议论不绝于耳。同学们的物质生活非常艰苦,早餐只有稀饭,上两堂课就饿了,勉强靠每桌一小盘煮黄豆补充营养。但是光明山上的文化生活却十分丰富多彩。学校设置有音乐、体育专科,这更帮助了文体活动的开展。体育设施很完备,连棒球、垒球都有。1943年举行的全校运动会是当年的一件盛事,引起我的兴奋程度不下于五十多年后我在北京观看亚洲运动会。体育运动成风,离蓝田后还相沿成习。在国师由涂文教授各花了一个学期时间教的太极拳和踢踏舞,我至今还能打能跳。与此同时,一场场演奏会上的歌曲使我终生难忘。除了那许多使人热血沸腾的救亡歌曲外,还有音专唐学咏博士谱曲的国师院歌(廖世承先生作词)和《神曲》,以及美国《一百零一首名歌》(One Hundred and One Best Songs)歌集所载的许多优美动听的英语歌曲。半个多世纪后,我和我爱人周缮群还经常带着怀旧的情怀追忆和哼唱其中一些名曲,还在一些城市的书店寻找这本歌集,均无结果,想该书已绝版。此外,那时话剧在国师特别流行,特别令人着迷。一台台名剧如《北京人》《雷雨》的演出都是大事,演出之前使人焦灼地期待很久,演出后大家又要谈论很久。莎士比亚的名剧《罗密欧与朱丽叶》英文本的片断也曾搬上舞台。经常在话剧中扮演主角的同学(我现还能举出他们的名字)简直成了院甚至整个蓝田学生们心目中的偶像。演话剧的传统一直保持到南岳。1947年夏我们年级毕业离校前,欢送和告别的是两台话剧——《复活》和《万世师表》。
文化明珠蓝田
国师创办前后,长沙许多历史 悠久的著名中学也纷纷迁往蓝田,如长郡、周南、明宪、妙高峰等。这些中学也吸引了一批名牌教师,如相少岩、周世钊、黄培心等人以及一批接一批的学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国师自办的附属中学,在大学部的呵护下,很快就在全省出了名。国师附中的教学质量被认为是最过硬的,大学录取率冠全省。国师还开办了民众教育馆和民众学校,对普及普通和成人教育起了良好的示范作用。蓝田成了湘中的教育中心,同时文化氛围日益浓厚。图书和出版事业几乎从一片空白发展到一派繁荣的景象。书店和出版社应运而生,林立于小街两侧。我还记得有一家文化服务书店,门面较大,能买到不少在桂林、重庆等地出版的文艺书籍。我在那里买到了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和林语堂的名著《生活的艺术》。出售课本和教学参考书的书店更多,我的中学物理老师就开了一家“学余编印社”,不仅出书,也卖书。我还记得有一家出版社叫“公益印刷公司”,出的书不少。我手头还保存着一本当时在本地出版的汉英词典,厚达七百余页,虽用纸较差,但印制水平和编辑质量均佳。可惜词典的封面和版权页残缺不全,无法证实出版单位。连这样的汉英混排的中型词典都能出,可见当时编辑出版水平确实不低。这里可看到国师的影响和推动作用。战时在蓝田几乎没有什么电影可看,我只在火车站广场看到过用小机器露天放映的《荒江女侠》。但是,在国师的示范和具体帮助之下,蓝田各中学演话剧之风却盛行起来,特别是在周南、明宪两家女中。那时一校(特别是国师)有演出,全市奔走相告,学生蜂拥而来,风雨无阻。我还记得冒着大雨去周南女中抢看名剧《家》的情景。就连长郡这样的男子中学也在车站大厅公演过歌颂岳飞的《精忠报国》。歌咏队和合唱团也到处组织起来,各校校园和街头不时响起慷慨激昂的抗日歌声。1943年左右,蓝田本地办起了一家报纸,文艺副刊是我一位好友编的,他把我和几个爱好文艺的同学计算在内正好七人,因此副刊起名为《七弦》,可惜我这根弦未起多大作用。总而言之,说蓝田已从文化荒漠变成文化明珠并不为过。

廖世承院长与国立师范学院附中部分毕业生合影
国师,我的家
蓝田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四年半的中学时代和国师的头一年都是在那里度过的,真是“日久识乡音,重添故里情”。而国师从蓝田时期起,完完全全地可以说是我的家。这种缘分和渊源是多方面的,不仅只是学生与学校的关系而已。首先,我母亲柳瑾也是国师的教职员。她早年毕业于长沙稻田女师,是较有经验的小学教师。我考入国师的前一年,她就进入国师民众教育馆位于六亩塘的民众学校任教员兼主事。那时在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我的父亲早已不幸在外地遇难,我们母子二人相依为命,六亩塘国师民校就成为我的家。说来也巧,幼年失学的我的姐夫王宝庆正由于在国师民校成人班学习成绩优良得到我母亲赏识而得以与我姐姐何智圆缔结姻缘。到1944年学院紧急疏散撤离蓝田时,民校随之解散,母亲失去工作,彷徨无计恐母子离散时,国师转聘她为校部总务处职员,这样她就有了名分和收入,得以同我一起迁往溆浦新校址。此后直至南岳,她住的宿舍一直是我的家,母子二人同以学校为依托。缮群毕业于国师附中,是国师英语系1947年入学的学生,而她的父亲周邦式教授是教过我逻辑学、伦理学的老师,她姐姐周范群也毕业于国师国文专修科,在校时是演话剧的主角。很巧,我岳家同样与国师结了不解之缘。
至于我个人,从蓝田光明山起,在校四年,我这个在山窝里学英语的土孩子,幸遇良师并受到良好校风的陶冶,较扎实地打下了英语和其他知识的基础。毕业后刚二十岁就能在新独立的印度的大使馆独力承担外交文书的笔译。解放后,我在外交部和驻外使馆工作多年,在党的亲切关怀和培养下,在思想和业务上都有新的进步。后来进入翻译出版界,主要从事联合国文献的翻译审校工作,也去联合国机构工作过,同时还翻译审订和组织出版其他一些译作。在这些方面,我对党的事业做出的贡献是微不足道的,却受到了国务院的奖励。这荣誉,我深感受之有愧,但这也可说是我能给母校带来的一点回报。
1998年,我们夫妇二人返湘参加湖南师范大学建校六十周年庆典。看到昔日的国师已发展壮大成为三湘大地上更加辉煌的重点学府,我不禁万分激动,泪流满面。从蓝田起,国师是我在乱世的家,现在师大是我们在盛世更大的家。返校真有“少小离家老大回”之感。1944年逃离蓝田时曾作过两首《菩萨蛮》,把自己比喻成“飘零烟雨中”的“孤鸿”。现在“换了人间”,心情也变了,今重改此词中的一阕(仅得留头两句),作为此文的结尾:
涟水戏波游子悦,光明山上弦歌迭。少小沐春风,老来无限情。麓山桃李艳,恍若蓝田现。日暖玉生烟,悠悠六十年。
(本文写于2003年,作者系英语系1943级校友)

 学校首页
学校首页  校友企业家联盟
校友企业家联盟